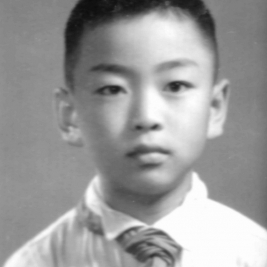我是在清华园长大的,记事时候,家还住在一区;后来搬到了北院住了好几年。我开始上清华附小时就住在北院,每天上学要从北到南,经过图书馆、大礼堂和二校门,几乎穿过整个清华园。大概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家又搬到了新林院,新林院离附小仅一步之遥,上学近多了,我家在新林院一直住到“文革”时期。1965年我从附小毕业,初中考上了北大附中,每天又要穿过中关园和科学院去黄庄上学。1969年我去东北插队,家里也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在清华没家了。后来再真正回到清华园是多年之后了,再后来出国留学、工作、定居,离清华园是越来越远。
北院现在已经不复存在,2006年我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做讲座,还特别去北院的原址看了看,岁月痕迹似已无处追寻,令人唏嘘不已。民国时期北院最早是给美国外教住的,也是外国人设计的,质量上乘,房子不大但每一栋房间很多,连仆人房间都有。北院不是中国传统的住宅,应该算是西式和中式风格的奇特结合,内装讲究,坐式马桶,房间大小不一,错落有致,都是地板,大玻璃窗,外面有百叶窗遮风挡雨;前边可以种种花草,建个葡萄架,后边还有个小院子,背后是矮矮的围墙,再过去就是清华的学生宿舍楼了。北院的中心有一个我们这些孩子称为“山”的土包,有棵孤树,土包上面还有战时碉堡的遗迹;旁边是个洗衣房,那时候每天都在外边晾床单、被单,白布翩翩,漫天漫地,层次分明。北院曾是清华美国教师和中国教授的住处,我家在北院时那里还住了不少名人,比如朱自清的遗孀陈竹隐,经常有大吉普车来接她去开政协会。
后来北院住的都是清华的教工,一到上学年龄,孩子们大都上了清华附小。附小离我们北院很远,大家都一路走一路玩着去,好像比现在上学的孩子快乐多了。我当时在北院的发小有李文浩和后来和我一起上了北大附中又去东北插队的卢琳,他们两家都是大家,都有5个孩子,我们也都曾是清华附小“校友”。李文浩和卢琳入学时间比我早一年级,我因为上了清华附小的实验班,在中学时就和他们同级了,算是赶上了老三届里面最小的初中1968届。命运弄人,早上了一年中学让你的人生轨迹和你的同年人大为不同,比如北京“文革”时的中学生里,虽然大都是下乡知青的命运,1968届插队的多,1969届则大批去了东北兵团。
新林院也是一栋一栋的住宅,档次也比较高。现在那些住宅还在,但大都已经看上去破败不堪。我们住的新林院一号住了5家人,两户是海归,一是从美国回来的、一是从印尼回来的;其他则是一般的教工了。新林院的好处就是离附小非常近,而且院中心还有个体育场,我们常昏天黑地在那里踢球。住到新林院后,我的玩伴主要是一号的几个孩子,隔壁双胞胎的钟氏兄弟,还有我在实验班的好友唐伟。在新林院的时光有“文革”穿插其间,虽然有过抄家、打人的恶事发生,对我们来说还算得上是自由的时期,后来更因为不用上学,到处去玩,比如,夏天每天骑车到颐和园游泳,到圆明园找琉璃瓦,为养鸽子作招引物,还为养鸽子的事打过群架。相形之下,在附小的生活因为发生在“文革”前,比较规范,似乎没有那么鲜活,记忆比较模糊,当然也还是有不少值得回忆的。
清华附小是个好学校,有清华的底子和招牌,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高,老师都非常敬业,师生关系融洽,当然学生的素质也好。蒋南翔主持高教部和清华时期,对附中和附小都很关心。附小的实验班就是当时“十年一贯制”新想法的试点(十年一贯制的意思就是小学5年,中学5年完成大学前的教育)。我们1960年进附小上一年级,但是1965年就毕业了,小学跳了一级,在附小的历史上大概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批学生。现在大家都年过花甲了,想起附小的往事,一下子就可以体会出什么才是“百感交集”。
对我来说,附小的老师中记得最清楚的是年轻的张国蕙老师,当时刚刚分配到附小教书,比我们这些小毛孩子也大不了多少,张老师善良美丽,给我们印象最深,她教的11到19的乘方口诀,我至今还记得,这也是我在附小学习时期还记得的不多的几样东西。许多年后的1980年代,我和李文浩回附小探访,还见到了张老师和另外几位现在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教音乐的男老师刘秉钟(大刘),岁数当时就不年轻了,声音很好,琴弹得好,有肺病,经常用手绢护着嘴咳嗽;后来听说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了,自杀未遂,人生悲剧。我在附小时瘦瘦小小的,算是不起眼的学生,胆小怯场,也没有很多朋友;但是我学习成绩还好,作文比赛时还得过一次一等奖,奖品至今还记得,是一本翻译的苏联小说《带枪的孩子》。我喜欢语言类的课程,当时曾经对相声情有独钟,后来据老师说我曾经强烈要求给我们机会上台说相声;我是不记得了,但应该是有这回事,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讲故事。后来插队时,在工厂当工人时,给大家讲《三国》《水浒》、“说岳”都是我的强项。而且最后大学本科学的是文学,这底子大概是在清华附小就打下了。
我在附小时还出过两次事故,至今记着;一次是由于当时非常淘气,在附小的大铁门上荡着玩,结果铁门撞到门柱上把我的右手食指挤掉一块,当时疼的我撕心肺裂的,一下子就晕过去了,被一位老师抱着送到医务室,现在我的右手食指还少一块,算是附小给我的纪念。还有一次是因为我低血糖在全校活动时昏倒了,后来也是老师把我送到医务室,我醒来时已经在校医院了,附小通知我妈妈,把她吓坏了,回到家给我做了一次鸡蛋炒饭,那是我此生吃过的最香的蛋炒饭了,也算是拜附小所赐吧。
当时附小的校舍相对简陋,没有几所像样的大房子,高年级的教室是两层的,我们的教室是平房,房前有秋千,总有几个能耐大的学生在那上面飞来荡去,我那时胆子很小,对那些能把秋千荡到九十度平飞的孩子非常羡慕。我还记得我们的教室窗外是一丛丛黄色的迎春花,有时在教室里上课,看着阳光灿烂下的怒放的迎春花,就想逃课出去玩。这大概是很多孩子在学校生活中都有过的白日梦。我的“家庭出身”在知识分子集中的清华大学也算是比较“差”的,所以入少先队也算晚的,到后来我的红领巾也总系不好,我的那张附小时期带着红领巾的“标准像”就很掉价,红领巾系得就像卷在一起的围巾;所以这也连累了我,直到后来我在加拿大教书,西装领带也一直打得不怎么样。
我们这批学生在1965年毕业,当时的“小升初”就考两门课,语文和算术,当时我们附近的中学以一零一中学为最好,然后就是清华附中,大多附小的同学都首选清华附中;我觉得我考试考得不错,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能进清华附中,而是上了远在黄庄的北大附中。当时我那届上北大附中的清华附小的校友只有五六位,熟悉的就三位,卢琳和李昕不但算是发小,还是我后来的插队同学,黄培和我在一个班;不过这样就和很多从附小升附中的发小分开了,当然后来大家更是天各一方了。1968年大规模知青下乡的时候,我们北大附中有一次在北京站值勤,正好送别我的很多清华附小后来到清华附中的朋友,像唐伟他们就都去了陕西延川。诗人食指(郭路生,就是不朽诗作“相信未来”的作者)曾写过一首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描绘知青离别北京的氛围和心境,传神动人;当时我还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但看着朋友们离别远行,心里确实是酸酸的。命运无常,没想到送走去陕西插队的朋友们没多久,1969年4月的一天我们也被绿皮火车送去了东北。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的东北插队的同学去的都是吉林洮安,我们在瓦房公社,清华附中去的是野马公社和那金公社,就是到了北大荒大家的集体户也相距不远;前几天我偶然用谷歌地图浏览东北,还看到了那些熟悉亲切的地名。但那次离开了清华园,离开了北京,一走就是好多年,人生的故事在不同的场景里继续上演;说到头,清华附小还是我们走向真正人生的起点。
我说清华附小是个好学校,是因为给我留下的记忆绝大部分是美好的。“文革”时期清华附小一定也有很多伤心的事,但那时我们都已经离开了。相形之下,我的中学母校北大附中,因为是“文革”时期的经历,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比较复杂了。现在想想,人生一世,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还是多记着那些美好的事情吧。
谨以此文纪念清华附小百年校庆。